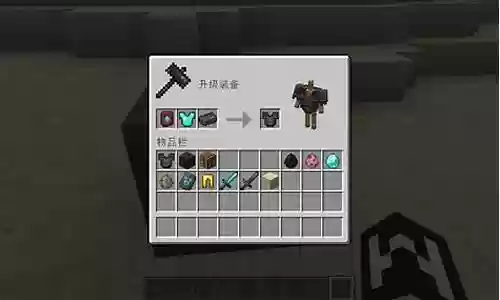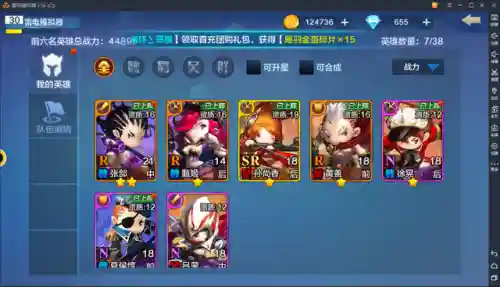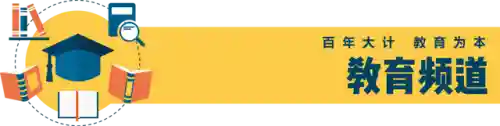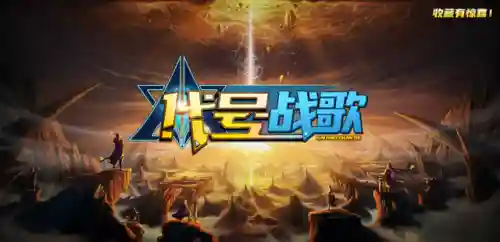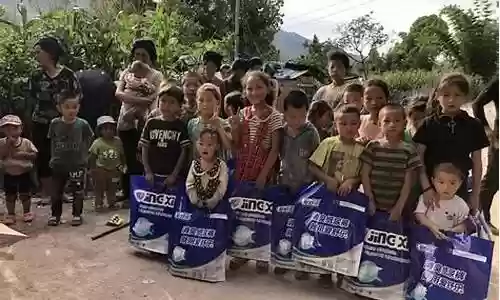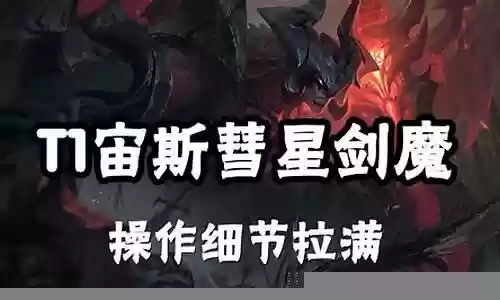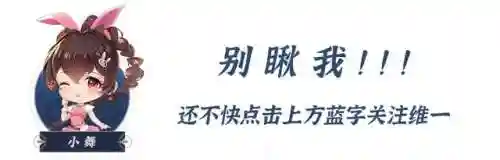孙策7300阵容(4400关主孙策阵容搭配技巧)
相比于江东学者,流寓士人明显更受孙权重视。表面上看,这与江南、江北的学术风尚有关;背后反映的,却是淮泗人与江东人对统治者的态度差异。
东汉末期,大量北方士人流寓江东,他们凭借自身的文化素养与政务才干,在军事、政治、文化等层面为孙吴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关于士人流徙与南北文化传播问题,唐长孺、葛剑雄、曹道衡、王永平等学者均做出过精辟论述,对本文立论深有启发。
梳理《吴书》及相关史料时,我注意到孙吴政权中存在的一个特殊现象,即流寓士人在学术、文化方面存在垄断现象。
人所共知,孙策兄弟建立的江东政权,是以淮泗集团(即江北地主)为核心支柱,其性质与统治西川的荆楚集团高度相似。
所不同者,在于孙氏后来完成了统治集团的江东化,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与扬州豪族的妥协与合作,蜀汉政权则未能与益州大族合流。
以周瑜、鲁肃、张昭、张纮为代表的淮泗文武,一度垄断了孙吴的军政大权;与此同时,流寓士人也垄断了东吴的文化机构,他们不仅充当孙策兄弟的御用文人,也大量出仕于东吴的学府与公族的幕府之中。
这一点十分值得注意。因为吴郡四姓与会稽四姓,大多具备传家经学,其中不乏优秀学者,但无论是虞翻、陆绩,还是张温、暨艳,虽然出仕孙吴,但对孙氏公族的学术文化影响十分有限。在孙氏子弟的幕府当中,罕见江东学者的身影。
孙氏在教育层面所倚重者,主要是江北的流寓士人,可知在文化层面上排斥江东子弟。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注意。
本文共 7300 字,阅读需 14 分钟
江北士人对江东的文化影响
中古时代的学术文化传播,主要借助士人的流动来实现。在治世与乱世,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。
和平时代,文化传播的途径,或者是中央王朝派遣学官到地方传道;或者是文化落后地区的士人到文化发达的地区游学。
战乱时代,文化传播的途径,主要表现在文化先进地区的士人、向文化落后地区进行被动迁移。这一点在汉末乱世表现得尤其明显。
注:文化传播的路径差异,见王永平《侨寓士人代表的文化修养及其兴学传教》。
汉末丧乱,导致大量的中原士人逃往边地,辽东的公孙度,交州的士燮,荆州的刘表,益州的刘焉,均吸纳了大量的中原学者;江东地区同样如此。
天下大乱,(管宁)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,遂与(邴)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。(公孙)度虚馆以候之。--《魏书 管宁传》
(荆)州界群寇既尽,(刘)表乃开学立官,博求儒士。--《英雄记》
(士)燮体器宽厚,谦虚下士,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。--《吴书 士燮传》

刘表招徕学者,开立官学
从可见的史料记载看,豫章太守华歆(籍贯青州平原)、会稽太守王朗(籍贯徐州东海)、扬州刺史刘繇(籍贯青州东莱)等外州出身的地方牧守,本身就是著名学者,他们在任官期间又大量招徕江北旧人,在扬州形成了一个个小型文化圈。
华歆北返时,“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”,可谓壮观。
(孙)权悦,乃遣(华)歆。宾客旧人送之者千余人,赠遗数百金。--《魏书 华歆传》
除了汉廷任免的牧守之外,还有大量流寓学者,投效于孙氏幕府。
比如彭城的张昭、严畯;广陵的张纮、秦松、陈端、卫旌;临淮的步骘、鲁肃;琅琊的诸葛瑾等人,均是彼时大儒。张昭、张纮有传家经学,诸葛瑾等人亦曾游学京师,他们为北国学风在江南地区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张昭字子布,彭城人也。少好学,善隶书,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,博览众书。--《吴书 张昭传》
严畯字曼才,彭城人也。少耽学,善诗、书、三礼,又好说文。避乱江东,与诸葛瑾、步骘齐名友善。--《吴书 严畯传》
(诸葛)瑾少游京师,治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--韦曜《吴书》
江南与江北的学术风气不同,江南流行的是今文经学,江北则流行古文经学。
经学,即儒教经典学说。今文经与谶纬等“内学”联系紧密,讲究天人感应,往往将人事变动、王朝兴衰与天象异术相附会;古文经则重视文字训诂,与谶纬联系较少。
注:谶即预言,纬即对儒教经典的附会。东汉光武帝迷信谶纬,称之为内学。
今文经盛行于西汉,东汉时代逐渐式微,地位被古文经取代,直到汉末马融、郑玄等人“兼采今古”,二者之争才渐告平息。不过彼时经学已经衰落,即将被玄学所替代。
与中原不同,江东地区的学术风气,偏重于今文经学。唐长孺等人通过对虞翻(会稽四姓)、陆绩(吴郡四姓)等家传经学的分析,认为“江南流行的都是今文学说,与时代学风相背驰”。
注:江北与江南的学风差异,见唐长孺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》,王永平《孙吴学术文化风尚考论》。
淮泗学者以及流寓士人的学风,与江东地区呈现出相异的特点。
这些流寓士人大多有过在洛阳或中原地区游学的经历,张昭、严畯、诸葛瑾等人皆治《左氏春秋》、《毛诗》,有较强的古文经学色彩;程秉、薛综师从郑玄;混通今古,张纮精通今文经,但私下研修《左传》,也属于今古兼杂的学者。
薛综字敬文,沛郡竹邑人也。少依族人避地交州,从刘熙学。--《吴书 薛综传》
(张)紘入太学,事博士韩宗,治《京氏易》、《欧阳尚书》,又于外黄从濮阳闓受《韩诗》及《礼记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--韦曜《吴书》
程秉字德枢,汝南南顿人也。逮事郑玄,后避乱交州,与刘熙考论大义,遂博通五经。--《吴书 程秉传》

诸葛瑾治古文经
由此可知,流寓士人大多治古文经或博采众家;江东豪族则倾向于已经日薄西山的今文经。因此在文化层面上,江南学者难免受到江北学者的压制。
江北与江南的学术风气异同,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流寓士人垄断东吴文化的现象。
公族学术幕僚的出身问题
孙权执政期间,曾为公族子弟选择名师授业,大量学者因此出入孙氏诸子的府邸,并逐渐形成学术政治团体。
需要特别注意,出任公族学官与僚属的人士,绝少有江东子弟,几乎全部是流寓士人。这在江东子弟大量出任军政要职的历史背景下,显得极为反常,不能不引起注意。
以下分别罗列相关记载,以供参考。
(1)孙登幕府
孙登是孙权长子,也是东吴的首任太子。
孙权对孙登的栽培不遗余力,以陆逊为核心辅弼,同时挑选了徵崇、薛综、程秉等学者为太子太傅或少傅,又以诸葛恪、张休、顾谭、陈表为侍从,太子幕府繁荣当时。
(孙)权称尊号,立(孙登)为皇太子,以(诸葛)恪为左辅,(张)休右弼,(顾)谭为辅正,(陈)表为翼正都尉。--《吴书 孙登传》
陆逊是孙策女婿,也是江东地区率先与孙权合作的土著代表,因此得到宠信,属于特例。至于孙登幕府的其余僚属,则少有江东子弟。
徵崇是司隶河南人,精通《易》与《左氏春秋》,同时研习内学,属于今古兼杂的人物。
(徵)崇字子和,治《易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,兼善内术。。--《吴录》
程秉是司隶河南人,受业于郑玄。郑玄“博采古今”,与邴原齐名,号称“邴郑之学”,属于当时儒宗。
(程)秉为(孙登)傅时,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笃学立行。--《吴书 程秉传》
薛综是豫州沛国人,昔日在交州受学于刘熙(见前文引注),刘熙是郑玄的弟子,薛综的学术风气也可想而知。
至于“太子四友”当中,诸葛恪出身徐州琅琊,张休出身徐州彭城,陈表出身扬州庐江,三人均是淮泗集团成员,也均是二代子弟。诸葛恪是诸葛瑾之子,张休是张昭之子,陈表是陈武之子,可以视作青年贵戚集团。
以(诸葛)恪为左辅,(张)休右弼,(顾)谭为辅正,(陈)表为翼正都尉,是为四友。--《吴书 孙登传》
“四友”当中的特例是顾谭,他出身吴四姓,是丞相顾雍之孙。然而顾雍性情和顺,被孙权所信重,誉为“至德忠贤,辅国以礼”,属于扬州门阀的特例。
故丞相(顾)雍,至德忠贤,辅国以礼。--《吴书 顾雍传》

诸葛恪、张休、陈表、顾谭为太子四友
在孙登幕府中,还有谢景、范慎、刁玄、羊衜、胡综等人为宾客。
谢景、范慎、刁玄、羊衟等皆为(孙登)宾客。--《吴书 孙登传》
其中范慎出身徐州广陵、羊衜与谢景出身荆州南阳,胡综出身豫州汝南,皆为流寓士人。只有刁玄出身扬州丹阳,是太子幕府中罕见的江东子弟。
(2)孙和幕府
孙和是孙登临死时举荐的继任皇太子,基本全盘继承了孙登的政治势力。
除上文提到的诸多幕僚之外,孙和幕府还有阚泽、蔡颖、张纯、封俌、严维等学者,被称作“从容侍从。”
赤乌五年,(孙和)立为太子,时年十九。阚泽为太傅,薛综为少傅,而蔡颖、张纯、封俌、严维等皆从容侍从。--《吴书 孙和传》
孙和太傅阚泽是扬州会稽人,但他“家世农夫,居贫无资”,依靠替人抄书,“以供纸笔”。
(阚泽)家世农夫,至泽好学,居贫无资,常为人佣书,以供纸笔。--《吴书 阚泽传》
可知阚泽族望较低,与吴郡四姓(朱张顾陆)、会稽四姓(虞魏孔谢)等门阀之家大大不同。
或许是因为政治能量不大,因此阚泽受到的猜忌也较小。举例而论,孙权处理吕壹案时,一度与朝臣闹僵,阚泽则充当了中间人。
吕壹奸罪发闻,有司穷治,奏以大辟,或以为宜加焚裂,用彰元恶。(孙)权以访(阚)泽,泽曰:“盛明之世,不宜复有此刑。”权从之。--《吴书 阚泽转》
剩余诸人中,薛综出身豫州沛国,张纯出身扬州吴郡,其余人物籍贯不详。从孙和“好学下士,甚见称述”的记载,以及他的儒家化倾向来看,江东子弟对孙和的影响无疑强于孙登。
孙权对于公族子弟的江东化色彩十分反感,他认为儒家化的君主,容易被大族架空。这也侧面解释了孙和被废的原因。
(孙权曰)一尔已往,群下争利,主幼不御,其为败也焉得久乎?所以知其然者,自古至今,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,而不离刺转相蹄啮者也!--《吴书 诸葛瑾传》
(3)孙休幕府
孙休是东吴第三任皇帝,“锐意典籍,博览群书”。他在做皇子时,“从中书郎射慈、郎中盛冲受学”。
孙休字子烈,权第六子。年十三,从中书郎射慈、郎中盛冲受学。--《吴书 孙休传》
其中射慈是徐州彭城人,被称作“硕儒”,盛冲籍贯未详。
射慈字孝宗,彭城人,吴中书侍郎、齐王傅,著《礼记音》一卷。--《经典释文 序录》
以时代背景而论,江东地区不乏名儒,但孙权却刻意选择流寓学者充当皇子与公族的宾友,这确实十分反常,似乎孙权在有意限制江东人士对孙氏子弟的文化影响。
其实孙吴公族师从淮泗学者,存在深远的历史背景。昔日宗室孙瑜,起兵之初,“诸将宾客皆江西人”,江西即江北,指淮泗地区。
(孙)瑜字仲异,以恭义校尉始领兵众。是时宾客诸将多江西人。--《吴书 孙瑜传》
孙瑜出任丹阳太守时,兴办官学,以马普为儒宗,“使二府将吏子弟数百人赴其受学”。马普是兖州济阴人,属于流寓学者。
济阴人马普笃学好古,(孙)瑜厚礼之,使二府将吏子弟数百人就受业,遂立学官,临飨讲肄。--《吴书 孙瑜传》
宗室孙奂出任江夏太守时,亦“爱乐儒生,兴办官学”,仕进朝廷者数十人。
(孙)奂亦爱乐儒生,复命部曲子弟就业,后仕进朝廷者数十人。--《吴书 孙奂传》
虽然史书没有记载孙奂官学的人员籍贯,不过从他“命部曲子弟就业”的描述来看,很大概率依然是以流寓士人为主导。前文已述,孙氏部曲多江北人,因此选择江北学者充当教师,更加合乎逻辑。

孙吴宗室开设官学,临飨讲肄
综上所述,在孙吴宫廷以及公族幕府中,占据文化垄断地位的,实际是以淮泗士人为主体的流寓士人,罕见江东学者。
孙氏父子对江东学者的敌视态度
富春孙氏族望较低,文化素养有限,孙坚与孙策更是近乎文盲。由于文化问题,孙氏父子早年曾与江东学者有过牴牾,这可能是造成孙权排斥江东学者的原因之一。
孙氏家族务农为业,孙坚之父(一作祖父)孙钟“种瓜自给”,社会地位不高。因此孙权追祖庙时,仅限于武烈庙(孙坚庙)与桓王庙(孙策庙),再往上则不见祭祀——可知孙钟的瓜农身份,无疑令孙权感到难堪。
(孙)坚父名(孙)钟,因施瓜供异人而获吉地。--《异苑》
孙权不立七庙,以父(孙)坚尝为长沙太守,长沙临湘县立坚庙而已。--《宋书 礼志》
孙坚的文化素养较低,自诩“太守无文德,以征伐为功”,而且因为草莽出身,多次受辱。比如荆州刺史王叡便“言语轻之”。
主簿进谏,(孙)坚答曰:“太守无文德,以征伐为功。”--《吴录》
(王)叡先与(孙)坚共击零、桂贼,以(孙)坚武官,言颇轻之。--《吴录》
孙策的文化水平也十分有限,他粗通《左传》,但在名儒高岱的衬托下,自惭形秽,竟杀人泄愤,自卑心理暴露无遗。
(孙策)闻其善《左传》,乃自玩读,欲与论讲……策果怒,以为(高岱)轻己,乃囚之……策恶其收众心,遂杀之。--《吴录》
孙策效力于袁术时,曾与汉廷使者马日磾交谈,结果受到对方嘲弄,马日磾称“东方人(指江东人)学问不博”。
孙策虽然心中恼怒,却无力反击,只得求助于虞翻,希望借虞翻的辩才,来“折辱中原妄语之人”。
(孙策)谓(虞)翻曰:“孤昔再至寿春,见马日磾,及与中州士大夫会,语我东方人多才耳,但恨学问不博,语议之间,有所不及耳……故前欲令卿一诣许(县),交见朝士,以折中国(指中原)妄语儿。”—韦曜《吴书》
孙权粗通经传,自诩读过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记》,实际文化水平并不太高,被曹丕嘲弄为“吴王颇知学否”。东吴使者对此无力辩白,只能惭愧地遮掩为“我江东自有国情,吴王志存经略,不像儒生般寻章摘句”,实际是变相承认了孙权学问有限。
魏文帝善之,嘲(赵)咨曰:“吴王颇知学乎?”咨曰:“……(吴王)志存经略,虽有余间,博览书传,历史籍,采奇异,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。”--韦曜《吴书》

曹丕嘲赵咨:“吴王颇知学乎?”
在此背景下,孙氏兄弟受限于文化素养,对江东名儒天然存在抵触情绪。孙策杀害高岱,虽然借口“高岱诳惑众人”,根本原因,还是因为孙策的自卑心理作祟。
虞翻、陆绩的事迹,可以较充分地反映出孙氏的自卑心理,以及他们对江东名儒的敌视态度。
陆绩是陆逊族叔,“容貌雄壮,博学多识,星历算数无不该览”,属于江东地区的一流学者。
(陆)绩容貌雄壮,博学多识,星历算数无不该览。--《吴书 陆绩传》
但是陆绩出身吴郡四姓(顾陆朱张),其生父陆康又死于孙策之手,因此受到孙权猜忌。
孙权假意授予陆绩“奏曹掾”,又借口其出言不逊,将其贬至交州。名为太守,实是流放,陆绩郁郁而终,年仅三十二。陈寿对此十分惋惜,称孙权此举,无异于“贼害大贤”。
陆绩之于扬玄,是仲尼(即孔子)之左丘明,老聃之严周(即庄周)矣;(陆绩)以瑚琏之器,而作守南越,不亦贼夫人欤!--《吴书 陆绩传》赞语
虞翻出身会稽四姓(虞魏孔谢),曾是孙策的心腹僚属,但虞翻与孙权关系不睦,“犯颜谏争,性不协俗,多见谤毁”。
(孙)权既为吴王,欢宴之末,自起行酒,(虞)翻伏地阳醉(装醉),不持。权去,翻起坐。权于是大怒,手剑欲击之。--《吴书 虞翻传》
虞翻“少好学”,家传《孟氏易》,也属于江东地区的一流学者,最终遭到孙权流放,居交州十余年,客死异乡。
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(虞)光,少治《孟氏易》,曾祖父故平舆令(虞)成,缵述其业,至臣祖父(虞)凤为之最密。--《翻别传》
(孙)权积怒非一,遂徙(虞)翻交州。在南十馀年,年七十卒。归葬旧墓,妻子得还。--《吴书 虞翻传》
虞翻性格刚戾,多次使孙权难堪,因此被孙权称作“江东之孔融”。
(孙)权曰:“曹孟德尚杀孔文举,孤于虞翻何有哉!”--《吴书 虞翻传》
此处的孔融并非褒义,诸葛亮亦曾把来敏比作孔融,称“来敏乱群”。所谓乱群,即干预朝政,蛊惑人心。
诸葛孔明云:“来敏乱群,过于孔文举。”--《宋书 王微传》
由此可见,对待精于学术的江东士大夫,孙策“动辄打杀”,孙权则“性不能堪”。除非这些儒学士大夫出身卑贱(如阚泽),或者知晓时务,主动与孙氏合作(如陆逊、顾雍),孙氏才能够勉强容忍。
即使如此,在拟定朝仪,撰写文书、教育公族子弟等重要环节,孙权依然更加倚重江北士人。
举例而言,孙权利用张昭(徐州彭城)、孙邵(青州北海)、滕胤(青州北海)、郑札(豫州沛国)等人修订朝廷典制。
(郑)胄字敬先,沛国人。父(郑)札,才学博达,(孙)权为骠骑将军,以(郑)札为从事中郎,与张昭、孙邵共定朝仪。--《文士传》
滕胄(青州北海)、是仪(青州北海)、薛综(豫州沛国)等人“善属文”,也多次参与文书拟定工作。
(滕)胄善属文,(孙)权待以宾礼,军国书疏,常令损益润色。--《吴书 滕胤传》
孙权承摄大业,优文征(是)仪。到见亲任,专典机密。--《吴书 是仪传》
外交方面,张昭(徐州彭城)、张纮(徐州广陵)则充当了主要的书记官。
(孙权)每有异事密计及章表书记,与四方交结,常令(张)纮与张昭草创撰作。--韦曜《吴书》
张纮出身淮泗,党附孙氏兄弟,因此往往对文书加以润色,回护孙权的颜面。张纮曾撰文歌颂孙氏功业,书稿既成,孙权激动落泪,称“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”。
(张)纮以破虏(指孙坚)有破走董卓、扶持汉室之勋;讨逆(指孙策)平定江外,建立大业,宜有纪颂以昭公义。(文书)既成,呈(孙)权,权省读悲感,曰:“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!--韦曜《吴书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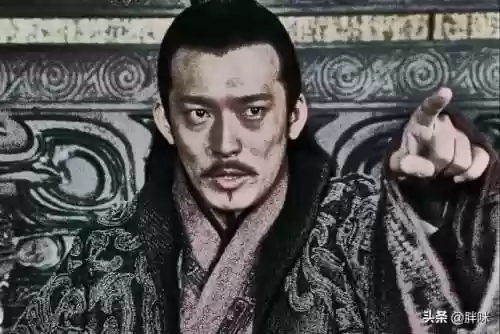
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
实际富春孙氏“种瓜自给”,处在彼时的社会底层,有何“家门阀阅”可言?可知此处无疑是张纮文过饰非,取悦主上。
张纮的文书内容虽然史籍无载,但大抵思路,无外乎“孙坚世仕州郡”一类的谄媚之辞,旨在抬高孙氏的门第族望。
(孙)坚世仕吴,家于富春,葬于城东。冢上数有光怪,云气五色,上属于天,曼延数里。--韦曜《吴书》
侧面也可以看出,相比于利用文化优势折辱孙氏父子的江东门阀,流寓士人更懂得维护孙权的尊严。
小结
江东地区门阀众多,亦不乏传家经学,但江东学者能够出仕孙吴政权者,却少之又少,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。
由于江东子弟在孙权执政中后期大量出任军政要职,因此他们在学术文化层面受到的排斥,便不能不加以留意。
江南与江北地区的学术差异,固然存在;但江东子弟受到排挤,恐怕主要是由于他们倚仗文化素养,轻慢孙氏家族,给孙权带来了极坏的印象。
同时,富春孙氏文化较低,因此对乡里宿儒,天然存在自卑心理。
不仅是孙坚、孙策与孙权动辄迫害儒士,东吴末帝孙皓,也因为“性忌胜己”而诛杀了“谈论每出其表”的学者张尚。可见孙吴君主的妒忌与自卑,是一以贯之的。
(孙)晧性忌胜己,而(张)尚谈论每出其表,积以致恨。--《吴纪》
孙权“性多嫌忌,果于杀戮”,自尊心极强。称帝后不肯郊祀,理由竟是“郊祀当于土中(指洛阳),今非其所”。他晚年甚至准备“亲征辽东”,欲“截鼠子之头,投之海中”,近乎病态。
(孙)权怒曰:“朕年六十,世事难易,靡所不尝,近为鼠子(指公孙渊)所前却,令人气涌如山。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,无颜复临万国!”--《江表传》
在此背景下,陆绩、虞翻这类不愿意与孙氏合作的文人,自然成为首要打击对象。这也能解释,为什么孙权看到张纮撰写的润色文书,会激动悲感,语无伦次,因为张纮确实维护了孙权脆弱的自尊心。
因此,无论是制定朝仪,典校文书,还是出任公族子弟的宾友幕客,孙权必然更加倾向于流寓士人。理由也显而易见,流寓士人背井离乡,无所依靠,对孙氏家族的依附性自然更强。
在江东政权的文化格局中,明线是“今文经”与“古文经”的学风差异;暗线则是“江北士人”与“江东门阀”对统治者家族的依附性差异。注意到这些信息,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东吴政权中流寓士人的文化垄断现象。
我是胖咪,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。漫谈历史趣闻,专注三国史。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、吉光片羽,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。
Thanks for reading.